得知《肿瘤药临床试验受试者小宝典》正在编写,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的创始人、南京天印山医院的秦叔逵教授爽快的答应作为新书主审。他殷殷切切关怀肿瘤患者,重视临床试验科普事业的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秦教授不但审阅全书,还参与访谈栏目,全面介绍了肝癌药物临床研究发展趋势,评价了联合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及肝癌药物研发的新思路,并寄语从业者努力攻克“癌中之王”,推动中国和全世界临床肿瘤事业。“干事业就得有雄心壮志,要勇于创新,还要善于创新。”
问:秦教授, 您好!原发性肝癌是我国人群高发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和致死率均居于全球之首。我国原发性肝癌诊疗目前处于什么阶段,有什么尚待完善之处?
秦叔逵:中国肝癌与欧美国家肝癌相比,具有高度异质性,其病因、流行病学特征、分子生物学行为、临床特点、治疗策略及预后显著不同。比如,我国原发性肝癌主要病因为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在欧美国家则主要与丙型肝炎病毒和非酒精性肝病有关。
在欧美国家,不可手术切除、不可接受局部治疗或局部治疗后复发进展的晚期肝癌患者的中位自然生存期为9个月,而在中国,该部分患者的生存期仅为3-4个月。因此,我们在诊断、治疗和研究上不可生搬硬套欧美的经验,需要认真地区别对待,必须开辟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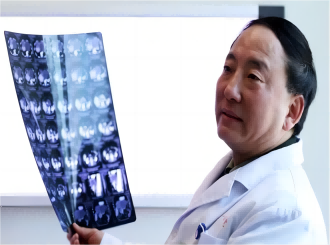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创始人 秦叔逵教授
中国一直高度重视肝癌的防治。早年吴孟超院士、汤钊猷院士等老一辈专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江苏启东市肝癌高发地区开展的流行病调查和防治研究为临床工作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老一辈专家的指导下,中国肝癌诊疗已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在外科领域,以樊嘉院士、董家鸿院士和沈锋教授等为代表的肝外科领域专家在手术技术上日臻完善。近年来,他们已不局限于外科工作,而是积极参与和主导了多项重要的临床研究,为肝癌诊疗作出巨大贡献。此外,在滕皋军院士及陈敏山教授等专家的带领下,我国肝动脉介入治疗和消融治疗等局部治疗水平也跃居世界前列。
得益于国家政府层面的重视支持、肝癌领域专家持之以恒的研究和肝癌的规范化诊疗进程不断深入等因素,我国肝癌的诊疗水平在国际上处于先进地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肝癌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水平已经进入了一个平台期,或者说是瓶颈阶段;在肝癌的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领域,特别是多组学研究方面,我国仍然非常薄弱,比如迄今没有找到一个驱动基因,也没有建立公认的分子分型,即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这是未来亟待努力的重要方向。同时,也希望更多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的学者能投入到肝癌领域,为攻克肝癌带来助力。只有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获得突破,肝癌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才能够克服盲目性而获得重大发展。
问:2022年9月,《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更新出台,作为我国原发性肝癌诊疗的指导性手册,该指南有哪些更新亮点值得注意?
秦叔逵:《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是由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肝癌专家委员会组织修订和更新的临床实践指南,在充分体现了肝癌诊疗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我国的经济、卫生事业发展现状等方面的国情和患者病情特点等,主要倾向于推荐肝癌治疗的基本策略和手段,成熟度较高;同时,新版指南也迅速反映了肝癌诊治的最新学术动态和进展,对个别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列举和引文讨论,并且谨慎推荐相关治疗策略。
新版指南中更新了诸多内容,比如在系统治疗方面,新增推荐了“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T+A方案)”、“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类似物(双达方案)” 以及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双艾方案)”作为一线治疗。
此外,新版指南推荐了2022年ASCO-GI会议上新公布的“STRIDE方案”,即度伐利尤单抗(PD-L1单抗)联合曲美木单抗(CTLA-4单抗)的双免治疗。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版指南中,还积极反映了中医药学方面的进展,推荐了淫羊藿素软胶囊(阿可拉定)用于一线治疗肝癌,还有通关藤制剂等。总之,《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依据循证医学证据,全面考虑中国国情、患者特点、药物可及性和相关不良反应等多方面因素,对肝癌的治疗选择进行了不同级别的专家推荐,对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问:在临床应用中,肝癌领域有哪些一线、二线药物作为主要的系统治疗手段?未来肝癌诊疗还可能会向哪些方向拓展延伸?
秦叔逵:肝细胞癌的一线和二线治疗药物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含奥沙利铂的系统化疗、抗血管生成分子靶向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现代中药制剂,和这些药物的联合治疗。如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成功开发与应用,极大拓宽了肿瘤传统治疗的边界,开启了肿瘤免疫治疗新时代。
未来免疫治疗的发展,将基于深入认识肿瘤与个体免疫系统间相互作用和肿瘤与器官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如何合理设计临床试验,联合不同免疫制剂或免疫联合其他治疗方式,值得进一步探索。我们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精确个体化的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应用于临床,惠及更多的肝癌患者。
问:晚期肝癌治疗,已从单药治疗走向了联合治疗,主要是免疫治疗联合靶向治疗等,您如何评价这些联合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未来免疫治疗可能还会带来哪些革命性的提升?
秦叔逵:纵观肝癌诊治和研究的发展史,15年前,晚期肝癌可谓无药可治,患者生存期很短,仅仅数以天计。2007年,索拉非尼的问世使得肝癌治疗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索拉非尼的疗效十分有限,但是肝癌治疗自此进入了分子靶向治疗时代。同期,随着EACH国际III期临床研究的成功,含奥沙利铂的系统化疗也成为了肝癌的重要治疗选择。但是此后十年间,晚期肝癌系统治疗停滞不前,许多项大型新药临床试验接踵失败。直至2017年才大为改观,新的靶向药物瑞戈非尼、仑伐替尼、卡博替尼及雷莫芦单抗的研究陆续成功,打破了10年的寂静。近年来,肿瘤内科、肝胆外科和放射介入科等多学科专家精诚团结,积极开展相关临床研究,特别是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PD-L1单抗及CTLA-4单抗为代表的免疫治疗,使得肝癌的治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当前,原发性肝癌系统性治疗已进入以免疫为主导的联合治疗新时代,无论是肝癌一线还是二线治疗,都有了更多选择。在一线治疗中,IMbrave150研究的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ORIENT-32研究的信迪利单抗联合达贝伐珠单抗、SHR-1210-310研究的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等重磅方案已相继获得阳性结果,而辅助治疗的IMbrave050研究也已宣告成功。这些研究表明,以PD-1/PD-L1抑制剂为主的联合治疗成为肝癌新的治疗模式。可以说,如今肝癌已脱掉了“癌中之王”的帽子。免疫治疗业已成为肝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以免疫治疗为主的联合治疗将贯穿于肝癌的全程,彻底改变了肝癌的治疗策略、格局、实践和结局。
必须指出的是,联合治疗需要有充分的研究数据证明其可以协同增效或降低副作用才能使用,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制定公布了联合用药的指导原则,应该学习遵守。总体而言,肝癌未来的治疗将以免疫治疗为主导的联合治疗,包含了不同药物的联合,也包含了药物与手术、放疗、介入治疗甚至消融治疗的联合,有望改变肝癌患者的生存结局。
问:虽然在临床上,不断有全新药物问世,但是在药物安全方面,您觉得应如何有效监测全新创新靶点药物的不良反应,最大限度地保护受试者安全?
秦叔逵:早在十五年前,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就重视到这一问题,专门组织成立了抗肿瘤药物安全管理委员会,期望在有效防治肿瘤的同时,提醒广大临床医师关注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提高患者临床用药安全性与耐受性。通过培训班、学术会议、制定防治指南和专家共识等一系列活动。如今,有关理念研究深入人心。
比如,已知免疫治疗与传统化疗和靶向药有许多不同,其治疗起效慢,不良反应也有拖尾效应。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的发生机制和临床表现常具有独特性:第一,可发生于全身多个系统和各个脏器,常见为皮肤不良反应、免疫性肝炎和免疫性肺炎等;第二,可发生于疾病的全程;第三,在处理上需要应用调节免疫或抑制免疫功能的药物。
早在2017年,CSCO免疫治疗专家委员会就在王宝成和张力教授的带领下,制定了相关专家共识,此后又补充升级为《CSCO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的毒性管理指南》,为临床医师正确、合理地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2020年,又制定发布《CSCO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临床应用指南》,有助于正确应用免疫治疗药物和加强对irAE的管理。总的来说,与传统治疗手段相比,免疫治疗可使抗肿瘤效果进一步提高,但同时,临床医生需对其独特不良反应的管理给予高度重视并且积极防治,将有效性发挥到极致,而不良反应降至最低。
在临床试验中,我们强调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GCP原则,特别注意新药的不良反应,确保受试者的安全;只有保证了受试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新药研发过程中的医学论理,才能在药物上市后的更大范围内保证病人的安全。由于进行临床研究时,通常都是随机对照试验,有严格的入排标准(比如挑选体质较好、相对病情较轻或病情简单的病人)和终止条款,及时实施药物警戒,以确保临床试验的安全顺利地进行,直至药物上市。而药物上市后,面对的人群更加广泛、临床情况更复杂,因此需要进一步考察药物的安全性,注意发现某些少见的、甚至罕见的不良反应,从而积累大量的数据,所以还需要上市后的研究、非干预研究或真实世界研究来支撑安全性。
问:未来在肝癌治疗领域,还有哪些新靶点和新作用机制的药物临床研究值得重点关注?
秦叔逵: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阿可拉定是一种从传统中药,也是天然药用植物淫羊藿中提取、分离、纯化得到的小分子药物,属于国家中药1.2类新药。基础研究数据表明,阿可拉定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可降低血液中IL-6浓度,抑制其下游信号通路JAK2/STAT3磷酸化,抑制PD-L1等的表达,影响炎症因子的释放,进而改善肿瘤微环境。II期临床研究发现,TMB、PD-L1、AFP、IFN-γ和TNF-α等指标都与阿可拉定的疗效密切相关。
联合治疗也是未来肝癌的新方向。在2007年索拉非尼上市后,至IMbrave150数据公布前,晚期肝癌的治疗一直没有跨越式的突破。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A+T方案)首次突破了索拉非尼的疗效瓶颈,使肝癌一线治疗进入了索拉非尼“后时代”。IMbrave150研究和其他联合治疗的研究改变了肝癌的治疗格局,为临床提供了疗效、安全性和可及性俱佳的联合治疗方案,同时这种联合治疗模式也改变了治疗理念,为肝癌研究的开展带来了有益启发。
问:您领导了许多肝癌药物的中国乃至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MRCT),能否举一两个您最为自豪的MRCT的例子?为什么感到如此自豪?
秦叔逵:从2000年开始,就我们原解放军八一医院全军肿瘤中心一家而言,就参加了310多项国际、国内大型多中心临床研究,其中牵头146项。在这些研究中,光是肝癌新药临床研究就有82项,这意味着全球著名的肝癌新药临床研究,我们中心都有参与。包括分子靶向药物的研究,从索拉非尼到如今的多纳非尼和阿帕替尼的研究;系统的化疗,从亚砷酸到含奥沙利铂方案的研究,和现在许多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研究,我们都积极地参与,边干、边学、边提高,在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同时,还组织开展了许多国内新药临床研究。前面谈到,中国肝癌发病率高,病死人数多,具有显著特点。所以,在参加国际、国内大型临床研究中,我们逐步积累了丰富经验,不仅贡献了较多病例,还有重要的中国智慧。
许多肝癌新药国际大型临床研究,只要有中国研究团队参加,我们无论在入组的数量、质量和速度上,都是名列前茅。比如,在当年索拉非尼的Oriental研究中,全亚太地区一共入组了226例受试者,中国大陆入组180例,中国台湾地区入组20例,其他国家加起来不过26例,即我们中国学者入组受试者的数量达到了整个亚太区总数的90%。又如,仑伐替尼的REFLECT研究也是一样,全球一共入组954例,中国大陆、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专家共同入组了288例,将近全部病例的1/3。
而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研究方面,中国也做了许多的贡献。比如,卡瑞利珠单抗二线及以上治疗晚期肝癌的临床研究,在短短1年时间内,我们完成了入组220例,获得优良的结果,期间得到了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的指导和支持,已在今年3月18日获得了批准新的适应症。
再举一个例子,在2021年6月初的ASCO大会上,全球学者共投稿6,300多篇文章,只有3篇肝癌研究被大会遴选为口头报告。其中,有两项报告,一项是"多纳非尼对比索拉非尼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开放标签、随机对照、多中心Ⅱ/Ⅲ期临床研究(ZGDH3试验)”,还有一项是“阿帕替尼二线及以上治疗晚期肝细胞癌(HCC)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的多中心III期临床研究(AHELP试验)”,都是我们中国专家主导的大型临床研究,高水平、高质量和获得了预期的结果。另外一项Study22国际研究,我们中国团队也是重要的参加者。所以说,一举囊括全部的口头报告,由此极大地震动了国际肿瘤学界。
就免疫治疗而言, 2019年,两项确证性III期临床研究CheckMate 459和KEYNOTE- 240却相继宣告失败,大起大落,给肿瘤学界带来了许多困惑。肝癌大型临床研究接踵失败的原因,除了药品本身外,更多是临床研究的设计、执行、质量控制和总结上出现了问题。以KEYNOTE-394研究为例,最初的想法是由欧美专家与中国专家共同牵头开展一项全球性确证研究,考虑到欧美国家与中国肝癌特征的差距较大,中国专家建议:分别开展两项临床研究,即分开东、西方人群;同时,要对研究终点、样本量、统计方法、抗病毒治疗以及中期分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优化调整。比如,针对西方人群的KEYNOTE-240研究是PFS 和OS的双主要终点,而中国专家考虑到肝癌的PFS与OS匹配性差,仅当HR<0.6时,PFS与OS才会紧密相关,所以KEYNOTE-394研究改设为单主要终点,且将HR值进行了调整。最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专家的考量非常正确。同时,这也提示申办方研发团队与临床医师互相沟通交流的重要性,双方共同合力方可取得试验的成功。
目前,肝癌的治疗策略、方法和结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年来,临床专家跟随吴孟超院士、孙燕院士和管忠震教授,不断学习。可以说,中国专家学者从过去“跑龙套”到今天的“弄潮儿”,已走在了世界肝癌诊疗和研究的前列。现在,我们已经不满足于“重在参与”,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肝癌患者的特点,积极牵头创新研究。
另外,我们的民族制药企业,像恒瑞、君实和百济神州公司等,都正在开展新药治疗肝癌的国际多中心研究,并且是由我们中国学者独立设计和牵头组织的,希望这些研究能为全球抗肝癌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当然,与国外的专家相比,我们还存在一些差距,需要继续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另外,与肺癌、乳腺癌等瘤种相比,肝癌领域取得的进步也还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将继续努力,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问:您对中国年轻的肝癌临床研究和临床研究者有什么期望?
秦叔逵:从中国肝癌药物治疗临床研究迅速发展来看,我国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有目共睹,尤其是近3年以来,超过了过去30年进展,晚期肝癌药物治疗的临床试验不断失败,也不断成功,新药陆续获批上市,如今已经极大地改变肝癌的治疗策略、格局、实践和结局。中国学者已经从重在参与,“跑龙套”,逐步成长为“弄潮儿”,走在全球肝癌药物临床研究的前列,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努力攻克“癌中之王”,推动中国和全世界临床肿瘤事业的蓬勃发展。
除了将治疗前移外,提高肝癌患者治疗效果仍然是重要的研究方向。目前肝癌一线治疗的最佳客观有效率(ORR)大约25%,中位OS约22-24个月。虽然已较以往有了显著提升,但是相较于肺癌和乳腺癌,仍然差强人意。比如,我国乳腺癌患者5年OS率高达93%,而肝癌患者仅为12.1%。此外,由于我国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已达中晚期,手术机会非常有限,而手术是早中期肝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最重要的治疗手段。
因此,通过转化治疗将不可手术切除患者转化为可手术切除的患者已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需要指出的是,肝癌患者同时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疾病,即基础肝病与肝癌,互相影响,恶性循环。部分肝癌患者可能因基础肝病恶化而发生病情恶化或死亡。因此,针对肝癌的系统治疗需要涵盖患者的基础肝病。肿瘤学专家应该虚心地向肝病学专家学习,与肝病专家精诚合作,一起积极控制肝炎、肝硬化、肝功能异常和防治相关并发症。
总体而言,今天针对肝癌的治疗手段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可以说肝癌已经摘掉“癌中之王”的帽子,但是其治疗效果仍不及肺癌、乳腺癌等其他常见肿瘤,因此肝癌工作者需要继续努力学习提高,不断缩小差距。
中国肝癌诊疗与研究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诊疗与研究水平提升未来可期。尽管近年来肝癌治疗进展明显,但在临床上仍然存在巨大而未满足的需求。首先,在预防方面,病毒性肝炎是导致肝癌的重要原因,如何防止病毒性肝炎的发生和传染尤为重要。因此呼吁广大群众积极接种乙肝疫苗、避免食用霉变食物以及戒酒。其次,在诊断方面,日趋提倡多学科协作模式(MDT)。如何建立完善肝癌的MDT团队以及对肝癌患者规范化诊疗面临的挑战之一。国家卫健委和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等已制定出台了多部临床指南和专家共识,旨在进行相关指导。第三,在治疗方面,目前晚期肝癌系统治疗的疗效已发展至瓶颈阶段。
今天,以抗血管生成药物和免疫药物为主的靶向治疗缺乏生物标志物预先筛选合适的患者,仍然属于“撒大网式”的盲目治疗手段,特别期待基础和临床研究的突破,以进一步提高选择性以延长患者生存,诊治研究中需要加强多学科专家学者的相互合作。相信在这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通过基础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的协同努力,未来肝癌诊疗和研究水平必将会大幅提高。
问:在您30多年的从医生涯中,不断改写我国肝癌研究和治疗的历史,回忆过往,什么是您孜孜不倦的为肿瘤患者接受治疗、参加临床试验以及为他们科普健康知识作出贡献的动力?
秦叔逵:第一,人生总会遇到重大选择,认准了就要走到底。立志从医,坚守在临床一线,是我自幼的心愿,乐此不疲。第二,干事业就得有雄心壮志,要勇于创新,还要善于创新。在攀登医学高峰中前行,是我的毕生追求。第三,身为人民军医,要有仁心大爱。救死扶伤,热情为患者服务,应该责无旁贷,义不容辞。